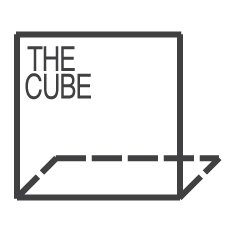陳界仁:《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

《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 超16mm轉DVD‧黑白‧局部有聲‧21分04秒‧三頻道錄影‧循環放映,2002 (圖片:陳界仁工作室)
作品背景脈絡與簡介
(文 / 陳界仁工作室提供)
影片的構想,來自一張法國士兵於1904年(或1905年)在中國拍攝的凌遲酷刑照片。(註1)
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三個受凌遲酷刑的人,被不同的歐洲人拍攝下來。這些照片曾被視為中國是「野蠻、殘酷」的證據,也曾被當作獵奇的異國情調,製作成明信片在歐洲流傳,或者被某些西方觀者聯想成是東方版的基督受難形象。1961年由於法國思想家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慾望的淚水》(Les Larmes d’Eros)一書中,以哲學性的觀點重新詮釋凌遲酷刑,而使凌遲酷刑與凌遲影像被西方知識份子廣泛地認識,喬治‧巴塔耶以「Eros」的「狂喜」狀態,詮釋受刑者處於「極限體驗」的觀點,也成為西方在討論凌遲酷刑時,最常被引用的論述。
近年來由於法國漢學家鞏濤(Jérome Bourgon)等學者的持續研究,凌遲議題更被擴延至東西方在法律、倫理、文化、哲學觀等的差異研究與比較,這也使得凌遲酷刑與凌遲影像,成為一個交織著多重視域與多重想像的混合體。(註2)
1996年陳界仁曾以電腦繪圖的方式,藉由改寫喬治‧巴塔耶談論過的那張凌遲照片,討論隱藏在「攝影史」內,還有另一種尚未被探討的「被攝影者的歷史」。
2002年陳界仁通過拍攝影片的方式,繼續對凌遲影像所可能擴延出的當代意義,進行更複雜的挖掘工作。對陳界仁而言,凌遲照片中承受酷刑的受刑者與歐洲人手中相機相互「對視」的那一刻,以及之後被定影下來的凌遲影像,不僅呈現了中國封建制度下的殘酷律法,也「預示」了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經驗──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其代理人的操控下,以推動現代化之名,對被殖民者/被攝影者所施加各種新型態「肢解技術」的生命狀態。
同時,陳界仁將凌遲照片中受刑者胸膛兩個闇黑的傷口,視為是兩個可以連結過去與未來的「通道」。影片中,陳界仁藉由將攝影機推入受刑者傷口的「通道」內,讓觀眾在受刑者體內「看見」──被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摧毀的北京圓明園、日本七三一部隊在哈爾濱設立的人體實驗室、冷戰時期的台灣政治犯監獄、跨國企業遺留在台灣的重污染地區,以及產業外移後的工廠廢墟。隨後攝影機再從受刑者的身體內部通過兩個傷口往外觀看到──歷史上的西方攝影師和當代失業勞工的群像。藉由這個進入受刑者體內,觀看到從過去到當代各種「被肢解」與「被廢棄」的建築殘跡,以及從受刑者體內往外看見當代失業勞工的連續性鏡頭,影片顯影出廣義的「凌遲酷刑」從未真正結束的狀態。(註3)
在凌遲照片裡,受刑者望著天際時,露出令人困惑的淺淺「微笑」──這個令人困惑的「微笑」,對陳界仁而言,亦是一個將無數觀看這張照片的觀者,捲入巨大困惑之中的漩渦,同時使得被捲入其中的觀者,無法不對受刑者何以會露出「微笑」的原因,提出各種可能的想像與企圖進行詮釋的欲望。陳界仁認為這個令人困惑與難解的「微笑」,不僅包含了喬治‧巴塔耶在思索凌遲酷刑時,認為其中存在著生命過程中重要的「兩種關鍵經歷──基督徒在十字架上的默禱和佛教徒在屍骨堆上的禪定」,一種從極度苦難中創造出超越愉悅的祥和狀態外,同時還存有佛教中另一種重要的「迴向」(註4)精神。
對於受刑者的「微笑」與「迴向」的關係,陳界仁認為「這個受刑者在承受凌遲酷刑時所露出的『微笑』,是一個無法逃逸的人,在被綑綁、被肢解、被拍攝、被灌食鴉片的恍惚狀態下,在似乎無法採取任何行動的狀態中,藉由『微笑』這個細微的表情和利用攝影師手上相機的定影功能,創造了令後來的觀者產生巨大困惑的影像;也由於這個巨大困惑的存在,使得受刑者的『微笑』影像──成為了『這個人』在被相機定影和被肢解死亡後,一個能與未來觀看這張照片的觀者,持續進行「對話」的影像。這是一個受刑者在幾乎『不可能』的極限處境下,所創造一個具主動性和無法被死亡與時間消解的『微笑/微型』行動。」
如同陳界仁認為受刑者的「微笑」,是一個試圖與未來的觀者進行對話的行動,在《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中,陳界仁通過對歷史影像進行後設想像的拍攝方式(註5),與被「無痛感」和「不可見」的當代治理形式置於新的「凌遲狀態」下的觀者,重新進行「再連結」與「再對話」,並在當代新自由主義、景觀社會、生命政治與反恐架構的政治語境下,將歷史上曾有過的另類微型行動,所可能再生產出的多重意義與啟發性,進行「再擴延」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