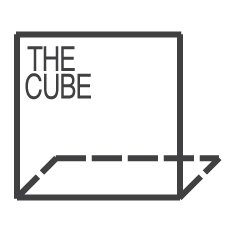Superflex
Superflex是由傑寇.芬格(Jakob Fenger)、羅斯莫斯.尼爾森(Rasmus Nielsen)、伯瓊斯傑尼.克利斯汀森(Bjonstjeren Christiansen)等人組成,他們計畫的主題在於經濟力、民生生產條件以及自我組織等等。這個團體嘗試要展現出全新的藝術態度。他們身處於一個異質、複雜的社會,而在他們組成計畫和發展小組時,也考慮到了這些「使用者」(會受到計畫影響的個人及團體)的特定興趣、不同的發聲機會、以及他們所關注的主題和對未來的預期。Superflex將這些計劃稱為是工具、產品或是系統,認為這些非藝術家所能獨有的資產,而必須要由他人來使用或再修改,才會具有意義。
近年來,Superflex曾參與的展覽包括2001年的第二屆柏林雙年展;2003年第五十屆威尼斯雙年展上的「烏托邦站」(Utopia Station);2005年第九屆國際伊斯坦堡雙年展;2006年第二十七屆聖保羅雙年展。此外,還有2002年在瑞典馬爾莫(Malmo)的羅希烏姆博物館(Rooseum);2005年在瑞士巴塞爾藝術館(Kunsthalle Basel);2006年在赫爾辛基的克雅斯馬當代藝術博物館(Kiasma);2007年在泰德美術館利物浦分館(Tate Liverpool);以及2008年在柏林的KW當代藝術館(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及台北雙年展。
(節錄自「2008台北雙年展」導覽手冊)
藝術家網站: www. superflex.net
展出作品: 〈金融危機〉(The Financial Crisis)
全片共分四段:「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你」(You),以及「老朋友」(Old Friends);此片為2009年Frieze藝術博覽會製作,由倫敦Frieze Films及英國公共廣電第四頻道(Channel 4)推出。
在這部由四個催眠片段構成的影片中,將金融危機視為精神性的症候,而試圖以催眠來治療受危機衝擊的個體。在催眠師的導引下,個體將想像陷入經濟崩潰的局面,而面臨恐懼、焦慮、挫折等心理狀態。
Superflex 成員傑寇.芬格談〈金融危機〉 (訪問者:鄭慧華、林心如)
問:請你先談談最新的影片〈金融危機〉(The Financial Crisis, 2009)。近年來,拍攝影片成為你們團體的實踐中重要的部分,這可以從〈水淹麥當勞〉(Flooded McDonald’s, 2009)和這部新片看出來。
芬格:我們一直都有用影片創作,但之前比較是以紀錄片的方式拍攝。而在四、五年前,我們作了〈活力果汁–瓜拉那〉(Guaraná Power, 2003)這項計畫;我們為此也拍了一些影片。它們是廣告片,虛構的短篇。我們確實在過去幾年更有興趣多拍一些片子。
問:為何特別對「影片」這個媒材感興趣?它有什麼特別的意含?
芬格:就我們向來的工作方式,我們從不會只拘泥於一種特定的媒材。我們一直視所作的東西而改變媒材:有時是飲料,有時是啤酒,有時是沼氣(Biogas)。在談論特定的東西時採取不同的媒材。這部新片的情況可能有點不一樣,因為它看起來更像傳統的電影。這或許是妳所指的意思。實際上,這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很大的改變,這部片的主要改變在於它有開頭和結尾,它不像我們作過的那種持續的長期計畫–像〈活力果汁–瓜拉那〉、〈自由啤酒〉(Free Beer)或有機瓦斯的情形,這些計畫以某種方式持續進展,而我們的新片則具有某種開頭和結尾。
問:為什麼這次想以「催眠」來處理金融危機這個主題?
芬格:首先,「金融危機」的概念關係到我們的這個訴求:這項危機是某種精神的問題。當然,因為人們正以種種方式而失業、賠錢,這變成了現實。但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這是個精神的危機。因此我們試著以一個古老的治療方式處理它:你進入某項災難的各個面向、透視恐懼、正視它,然後學著和它共處。
某方面,催眠的部分也關係到為何我們何以同時想到金融危機和催眠活動,因為它也是透過媒體所營造的東西;通常人們在真正感知到什麼事之前,就已經開始想著它。他們之所以感知到它,是因為他們談論它。於是這成為某種歇斯底里。所以,社會裡也大有著「催眠」的部分。
問:這是很情緒性的效應。
芬格:沒錯,即媒體操作這個議題的方式。的確,媒體持續談論這項危機,然後人們開始更明顯感受到它,所以這具有催眠效應。各種恐懼的情況也一樣,例如對恐怖份子的恐懼等。你開始談論某件事,然後它變成真實,就像某種催眠的階段。所以這就像某種疾病治療。此外,今天我們對事情的反應方式也很像催眠。每個人都被催眠,以至於相信資本主義、對恐怖份子的恐懼之類的事。
問:從你們的藝術實踐中,往往可以看到你們傾向於突顯各種資本主義經濟活動背後隱藏的法則或是其運作方式。你們運用各種形式和工具來轉化、表達和傳達這些通常是看不見的面向,將它們變成各種過程或行動。在你們實現這些計畫之際,最困難的部份為何?你們是否期待透過這樣的過程達到特定的結果,或是保持開放?
芬格:這和媒材的問題一樣:我們從不知道接著將以哪一種媒材創作。這並非既定,要看我們想走的方向,我們在不知道終點或去向之下前進。如果我們知道所有的答案,就沒有理由提出問題了。從〈活力果汁–瓜拉那〉這樣比較大型的計畫,或許比較容易了解。我們從基本的層面出發:我們在巴西和一些農民見面,他們跟我們談關於一間大型飲料公司和農民之間的權力鬥爭。農民覺得公司虧待他們。於是我們開始跟他們談他們的處境,〈活力果汁–瓜拉那〉就從這番對話中產生了。這是一場漫長而尚未結束的旅行的開端,其中,我們重新創造一切、重新界定脈絡。但我們不知道答案。
在〈金融危機〉一片中,也沒有解答。其中四場不同的催眠,它們像是將你置於某種情境,你在這裡看到可怕和災難性的東西,但我們不知道這將產生出什麼結果。當然,這同時是對於人如何自我組織、以及針對我們視體制為理所當然的批判。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還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對立,至少當時還有遊戲和正反兩方。但今天,現實已經改觀,所以,當體制瓦解時,我們還能夠相信什麼?
問:我們是否可以把「創造既有之外的另外選項」視為你們實踐的一項動機–如果不要說是直接的對立?
芬格:或許不只是創造另外的選項而已,而更是對體制的批判或進行干擾。再舉〈活力果汁–瓜拉那〉計畫為例,它是和資本主義一起運作的,但也在資本主義中提出不同的立場。它運用體制的機制來做不同的東西。
問:也就是激起某種反思或意識?
芬格:是的,但此外,也不只是這樣。這也是關於採取行動和去實際去做些什麼。像巴西的農民,他們知道問題和他們的侷限,他們通盤瞭解。但他們並沒有真的進入下一個層次,比如說:「去他們的,我們就做吧,就做這種飲料,然後走下一步。」在那樣的計畫中,我們起而行動。
問:是否可以說,你們的實踐有很強的行動主義特質?
芬格:當然,我們的實踐有某種行動主義的面向,但是在這個意義下:這種實踐實際上是跨入別的領域。它是行動派,不只是待在那裡等事情發生。它也是深入某個直接的現況,並作出行動。但再次說明,行動主義也是很危險的字眼,因為它和傳統的政治鬥爭混在一起,而我不認為這是我們所做的。
我認為重大的區別之一在於:政治行動主義者似乎心裡有答案、有特定的政治目標。我們則是在尋找,我們不知道我們想要的結果會是什麼,即使我們看起來找到了解答─它依舊還是個問題。所以在界定某個東西具有行動主義特質的時候,必須很清楚,我們做的其實有別於主流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