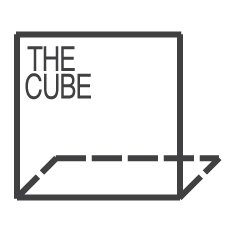2025聆聽雙年展「第三聆聽」作品簡介
1. Florence Cats / Lilja María Ásmundsdóttir (比利時/冰島)
《空氣》(AIR)(2025)
《空氣》是由藝術家Florence Cats(特雷門琴、人聲)和 Lilja María Ásmundsdóttir(赫爾達琴、人聲)創作的三聯作《空氣、水、火》的一部分。 這個新成立的二重奏從自然元素的特質中尋找靈感,探索廣泛的頻率,將電子音、弦樂與呼吸及口哨聲混合在一起。
「去年十一月,當我收到雙年展的邀請時,我正在雷克雅維克。我立刻產生了在戶外錄音的想像—那空間,那空氣中寂靜的口哨聲。空氣承載著聲音,是音波振動的媒介,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每天都在呼吸著聲音。 我最初的打算是進行田野錄音,但風太大了,我那廉價的設備不適合這樣的天氣狀況。 冰島人將廣闊戶外的浩瀚內化於心的方式也讓我著迷,這點可以從他們的凝視、藝術和音樂中感受到。 在聽了一場音樂家兼藝術家 Lilja María Ásmundsdóttir的音樂會後,我感到一種直接的共鳴,並提議在我下次到訪時與她合作。當我二月回來時,我們一起演奏,發現彼此在感性、音樂和心靈感應上都有連結。 我們決定創作一個三聯作,從塑造冰島的空氣、水、火的能量中汲取靈感,這三者在我們內心也對應著三個煉金術的焦點。我同時也是一名針灸師,在身體的特定穴位上扎針,以協調內在的能量流動與天地的流動。」
—Florence Cats
Florence Cats 的創作在聲音、音樂、詩歌和視覺藝術之間演變。她的研究關注與感知和記譜相關的那些難以捉摸的元素。她以實驗性的方式演奏特雷門琴,與人聲、呼吸、水、收音機和微型手工樂器互動。她同時也是針灸師和藝術策展人。2023年,她獲選為比利時新興聲音藝術家。她的發行作品基於田野錄音,是自由創作過程、對自然或其他藝術家開放的成果,作品包括:《shell I》(Ediçoes CN, 2025)、《Ys》(2022)、《We are now approaching Mo i Rana》(Ftarri, 2024)和《Correspondances》(Frissons, 2021)。她曾以作品《In the air》參與 The Asocial Telepathic Ensemble(Corvo Records, 2021)。
Lilja María Ásmundsdóttir是一位來自冰島的藝術家、作曲家和表演者。其實踐以探索協作創意為核心。她透過聲音和物質的雕塑性元素,創作裝置、影音作品和表演。這些作品被積極地設計用以促進持續的過程,凸顯想法如何從與材料、個人之間以及周遭環境的呼應中浮現。她的作品包括曾獲總統學生創新獎提名的聲光雕塑《Hulda》,以及她與舞者Inês Zinho Pinheiro 合作開發的活態聲音雕塑《Lurking Creature》。
2. Rachel S.Y. CHEN(新加坡)
《我的小小空間》(my tiny space)(2025)
與另一個人連結意味著什麼?連結始於創造一個微小的空間:一個溫柔、刻意的開放,其中可以容納差異,讓生命經驗得以相遇。這件作品收集了來自非語言自閉症個體及其家庭世界中親密的聲音痕跡。作品以《神奇音樂墊》(Magical Musical Mat, MMM)的田野錄音開始,這是一個旨在透過人際接觸和音樂促進連結的互動環境。非語言自閉症兒童和他們的父母以觸覺的、愉悅的、關係性的語言進行即興創作。咯咯的笑聲、《歡樂頌》的片段,以及層層疊疊的聲景,都源於溫柔的接觸:手指輕撫皮膚,手掌輕柔相握。這是一個存在活躍且自主選擇的微小空間。接著,一位非語言自閉症作家fifi coo的聲音出現,由藝術家(經fifi許可)朗讀。fifi以寧靜的清晰回應這片聲景,反思在創造生命微小空間中的愛。作品以一首鋼琴曲作結,該曲是為回應 fifi coo 的詩集《一個微小空間》(a tiny space, 2018)而創作,這本詩集分享了他作為非語言自閉症兒童的內心世界。Rachel的每一個音符都溫柔地安住於 fifi 詩歌的寧靜真實之中。 這首曲子本身就是一個fifi的文字與 Rachel 的聆聽相遇的地方:一個微小的、共享的世界,在那裡,Rachel短暫地被邀請歸屬於 fifi 的經驗之中。 在這些聲景之上,是 Rachel 的小提琴即興演奏,她深刻反思了透過與神經多樣性存在方式的親密接觸,在聆聽、學習和反思學習過程中的旅程。 《我的微小空間》的核心是邀請人們創造空間,讓各種存在方式的人們可以在共享的在場中相聚,在聆聽的行動中找到歸屬感。
Rachel S. Y. Chen 作品的核心是對人類連結的深刻探問:以真實、具身和包容的方式與他人分享在場。透過藝術、設計和研究,其實踐基於一個信念:親密的連結不需要相同、言語或常規。相反地,真正的連結在於歡迎差異、人們能深刻聆聽的空間中茁壯。透過聲音、動作和即興創作,Rachel創造了人們可以超越言語相遇的環境。憑藉她對神經多樣性社群社交生活的研究,以及對聲音即興創作的熱愛,Rachel設計了一些環境,溫柔地邀請人們探索親密、玩耍和共同創造。 在這些空間裡,聲音和動作成為集體即興創作的遊樂場。Rachel相信,即使是最分歧的世界也能找到和諧。她的作品邀請人們走出熟悉,仔細聆聽,並共同創造新的歸屬方式
3. Kaur Chimuk(印度)
《哀悼!來自虛空之地的日常精靈發酵儀式》(MOURN!NG: A FERMENTED RITUAL FOR THE MUNDANE SPIRITS FROM SHUNYOSTHAN)
Kaur Chimuk與Amy Singh X Pramukho Rupan X RENU的儀式合作,2025
想像一種長期的缺席——或許是誤聽/未聽/後聽——哀悼並非一蹴可幾,而是在我們最平凡的「片刻」中以停頓發酵。這種緩慢的發酵將時間提煉為記憶,使我們彎曲進入一個失憶開始萌動的空間。我發現這種情況如同Shunyosthan(註)的靈魂——Shunyosthan不是一個空間,而是一種未生狀態的熵,一個邀請我們的隨機性更接近混沌最高機率的開口。它不僅僅包含記憶,更使記憶成為可能。它不是記憶的場所,而是具有回應性的。此嘗試是探索南亞及東南亞反儀式的延伸實踐,連結超越其即時時間線的表演性概念。挑戰殖民框架,我們能否在不吸收其破碎結局的情況下,重新審視事件的流動?這個儀式被概念化為一個凝聚性發酵的過程,其中我對印巴分治記憶傷痕及其對重聚渴望的有限理解,被給予了空間去承載、停頓、風化,並透過協作來「織造成型」。此嘗試主要關注意象的死亡(不僅是印象,還有其背後之物),在其中信號變得模糊,記憶變得破碎,記譜法不足以捕捉時空,尤其是在這個後連續的真相中。 剩下的,是一種聲音的缺席。我們能閱讀這個嗎?更重要的是,我們能透過一種延伸的聆聽形式重新聽見它嗎?在這個過程中,我與我的盟友們合作,以反表演的姿態來處理後連續時態。人們不僅可以透過其流動來參與這首音軌,也可以透過其滲透——它對形成的矛盾,及其對本土發酵工具包的邀請,而非一種解構。至今,我試圖吸收這些碎片,並用一種研發方法論重新詮釋它們:逆轉(知識)和去文本(敘事)。在此過程中,儀式不僅是文化標記;它們成為激進(解讀為:關懷)的能動者,能夠掙脫殖民的規範框架。這種參與也是一個更大研究文選《南亞酷兒手冊》的延伸團結。
註:Shunyosthan是梵文,由「Shunya」(空性)和「Sthana」(處所、位置、狀態)兩部分組成
Kaur Chimuk(TA/黃)是一位跨二元性別者,將顛覆性的藝術研究作為一種工具,圍繞表演性時間再現進行凝聚性的協商。主要立足於南亞,他們在印度和孟加拉廣泛工作,同時在瑞典設有運營基地。主要合作對象包括Meteor International(瑞典藝術家網絡)、intrans aka intersectional network for transglocal solidarity(墨西哥-印度-英國的合作網絡)和zmayat(孟加拉與印度的開源合作社)。目前,Kaur正在進行《南亞酷兒手冊》的計畫,該計畫始於一個關於轉變相關詞彙的長期策展研究項目;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演變成一個沉浸式、後電影的跨學科檔案。
協力者
Amarpali Singh / Amy Singh 一位來自印度的詩人、表演者和寫作引導師,她的作品探索記憶、抵抗、渴望和愛的主題——通常透過印巴分治、女性主義和傳承的沉默等視角。她用印度斯坦語、旁遮普語和英語寫作,並以詩歌作為連結、記憶和重建的媒介。
Pramukho Rupan 他們的旅程從古典音樂訓練(rewaj)到挑戰音樂界圍繞「好」與「壞」概念的體制框架。Pramukho Rupan主要從事音樂家、製作人、思想家和聲音探索者的工作——其實踐者身份的正規訓練長達二十年。現在,他們渴望超越傳統結構,尋求日常音樂與人際間聲音記憶的和諧。
Renu Hossain / RENU 是一位出生於倫敦、具孟加拉血統的國際跨領域藝術家。她是實驗/電子/合奏作曲家與製作人、塔布拉鼓手、打擊樂手和策展人。
4. Čhoakkeladd(喀什米爾)
《Payam-e-Choakkeladd》(傷者訊息)(2025)
我們有一張地圖,我們有深入的路徑,我們進去,出來,然後在兩者之間翻滾,而你永遠不會發現。「Chokkelad」(喀什米爾語中的「受傷者」),常用於當地新聞廣播中,指暴力事件的受害者。《Payam-e-Chokkeladd》收集了當暴力行為持續在日常生活中上演時所產生的聲音。現在是新聞時間。Čhokkelad永遠感謝所有透過設備、關懷、時間、努力和關注為這個項目做出貢獻的人,並在此感謝Mu、Hi、U、E、Mo、Bu、Mukh、Ha、Ga、Sib和Eh。
Čhokkelad 立基於喀什米爾,其創作橫跨裝置、錄像、聲音、文本和雕塑等多種媒介。他們的作品旨在發展關於時間與虛空的詞彙,以對爭議地區的敘事化和歷史書寫提出質疑。
5. 莊力銓(新加坡)
《在任何一天》(On any given day)(2025)
在任何一天,一座城市都在它自身遺忘的聲音中嗡嗡作響。芳林苑,這個曾經是強制分離和命運未卜之地的地方,如今已被吸納進日常生活。1942年,它見證了決定誰能自由行走、誰將消失的甄別。由誰施予?從誰奪取?在莊力銓的《在任何一天》(2025)中,這是一部取材自芳林苑田野錄音的聲景作品,歷史與當下透過聆聽在此交匯。創作的行為本身就是一場挖掘,發掘出一個被重新利用和再開發場域的痕跡。他祖父從死亡中天真逃脫的故事,縈繞在作品之中,被摺疊進城市的聲景裡。我們是倖存者的後代。聆聽,是為了抵抗遺忘。發聲,是為了紀念那些給予我們今日的人們。
莊力銓(生於1975年)是一位對哲學、文化與藝術充滿熱情的新加坡作曲家。莊力銓在音樂與聲音領域的職業生涯始於90年代末,擔任作曲家與聲音藝術家,與劇場、舞蹈、口語、建築、電影製作、設計與視覺藝術等領域的實踐者合作。他的創作產出包括音樂作曲、聲音設計、田野錄音、聲景作曲、特定場域藝術、裝置、自由即興,以及探索不同表達模式對話與聲音詩學的協作作品。
6. Mariana Pinto Coelho Dias(葡萄牙)
《未聞之軀的共鳴》(Resonances of an Unheard Body)(2025)
透過聲音,身體超越了其可見的輪廓。順著這條思路,我們可以說「聲音」是我們身體的延伸。這個反思引導我們質疑人體的延伸極限:一個身體能延伸多遠?誰和什麼是它的一部分?它的存在層次有哪些?作品《未聞之軀的共鳴》運用聲學生態學的原理,並將人體視為一個未被發現的聲景,旨在突顯「聲音」與「聆聽」在感知我們存在中不可見層次的重要性。其目標是質疑人體的傳統界限,使其變得集體、互聯,並能滲透到他人及周遭的聲音環境中。同樣地,這件作品探究身體與聲音捕捉技術設備之間的關係,視其為擴展我們對世界感知的基本要素。科技是讓我們能夠發現並航行於身體存在所有層次、組合並平衡它們的資源。透過科技,我們可以意識到,即使我們表面上無處所在,我們卻可以存在於身體所延伸的任何地方。一個具有可塑結構、像水一樣,隨自然提供的條件改變其形狀並適應的身體。
Mariana Pinto Coelho Dias 是一位葡萄牙跨領域藝術家,其藝術作品涵蓋聲音藝術、實驗錄像、表演藝術及影音裝置。她專注於聲音研究,特別是聲學生態學,其作品源於一種渴望,希望能平衡我們感知世界時「聲音圖像」與「視覺圖像」之間的比重。她目前是里斯本美術大學(FBA-UL)的博士候選人、科學與技術基金會(FCT)的研究員,以及藝術研究中心(CIEBA)的成員。透過探索錄像表演與聲景作曲的實踐,她正在進行一項名為「人類聲學:透過錄像表演實踐聆聽『擴展(人)體』的聲景」的藝術研究計畫,該計畫尋求「視覺」與「聲音圖像」之間一致性結合的可能性,以感知一個「擴展(人)體」。
7. MycoDyke(印度)
《在上如在下》(As Above, So Below)(2025)
這件作品試圖為生態哀悼保留一個空間。我的實踐與我的生命,根植於真菌與腐生,透過它們,我開始理解死亡是一種過渡:一個滋養、重塑、再分配、再生的過程。但在2025年的夏天,德里經歷了一場提早到來且具災難性的季風。大量的樹木死亡,留下了樹樁、滴著樹液的傷口、裂開的樹幹和裸露的樹根。在真菌能開始它們安靜的分解工作之前,這些樹的軀體在幾天內就被砍碎並清除了。這是一個被中斷的過程:突然、停滯、未完成。沒有腐爛,沒有分解,沒有轉化。只有沉默。
這件作品就安住在這片沉默之中。在我的錄音裡,有雷雨的聲音和雨後的寂靜;有安靜、破碎的語音筆記和與樹木的輕聲對話;有孔雀的送葬哀鳴;還有一種感知地表下那些看不見的存在的需要。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篇具身的悼詞。一段低語。一種陪伴。對我而言,跨越物種界線公開哀悼,是一種政治性的聆聽——拒絕匆忙前行,拒絕遺忘。這正是「第三聆聽」所倡導的相互依存與「共享世界」的實踐,也是這件作品希望能體現的。
MycoDyke是Malavika Bhatia 的真菌化身,她是一位自學的田野真菌學家、藝術家和社群協力者。透過與真菌的互動,她將民族真菌學研究、社群實踐和理論框架交織在一起,以重新想像與地方、社群以及超越人類的世界之間的關係。她的活體裝置作品《腐朽與狂喜:分解二元對立》(Rot & Rapture: Decomposing Binaries)在2024年Gender Bender展覽中,將真菌培養物與散文詩歌結合,引導觀眾與真菌體進行親密對話,以探討消解作為通往流動存在狀態的途徑。她的藝術著作,包括《真菌詮釋學:學術森林中的(解)構》(Fungal Hermeneutics: (De)Compositions in the Academic Forest)和《「另類」地下:真菌酷異奇聞雜誌》(The ‘Other’ Underground: A Zine of Fungal Queeriosities),將學術概念轉化為情感敘事,提出對生態學中酷兒性的另類理解。藉由菌絲網絡作為隱喻和方法,她在班加羅爾科學藝廊、基蘭·納達爾藝術博物館、奇緣藝術節等地發展了參與式體驗,挑戰關於生態、社群和歸屬感的傳統敘事。
8. Hear & Found(泰國)
《大地之歌:來自泰國的原住民和聲(湄波基社群輪作農業的自然聲景)》(Earthsong: Indigenous Harmony from Thailand (Nature soundscape from rotation farming at Maeporkee community))(2024)
這段聲景錄製於泰國北部達府的湄波基(Maeporkee)社群,捕捉了克倫族傳統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面向:輪作農業,這是一種根植於自然再生與永續性的方法。輪作農業涉及克倫族人集體選擇一塊公共土地來種植水稻。在開始前,他們會舉行儀式向大地母親請求許可。獲得許可後,他們會清理植被、整理土地,並種植辣椒、香菜、南瓜等季節性蔬菜。年中左右,他們種植水稻,通常在十一月收成。這些作物能供應他們家庭一整年的所需。之後,土地會休耕三到七年,期間社群只會回來向土地表示敬意。這種循環方法自然地生產出不使用化學物質的有機食物,體現了再生農業的原則。克倫族人讓植物依季節生長,並收穫當季的產物,避免控制或傷害任何生物,展現了對生態平衡的深刻理解。不幸的是,由於土地權問題、年輕一代繼承意願下降、氣候變遷以及農業技術的快速發展,這項傳統知識在許多克倫族社群中正在消失。人們擔憂這種和諧且永續的生活與有機食物生產方式有朝一日可能會消失。Hear & Found 團隊對克倫族人為自己和後代保護這種農業方法的奉獻精神印象深刻,於2024年九月,在豐收前鬱鬱蔥蔥的綠色田野季節錄製了這段聲景。在這段音軌中,聽眾可以沉浸在鳥鳴、微風輕拂以及稻田隨風搖曳的沙沙聲等自然聲音中,這是他們永續生活方式的證明。這段聲景是他們《大地之歌》系列四段聲景之一,該系列交織了自然環境的聲音以及克倫族和克倫波族的音樂與歌曲。
Hear & Found 是一個由泰國藝術家Sirasar Boonma女士和Pansita Sasirawuth女士於2018年在泰國共同創立的聲音團體。出於為邊緣化聲音發聲的熱情,主要在泰國境內,該團隊創作沉浸式裝置和田野錄音,以彌合文化鴻溝並促進理解。他們的工作核心是與原住民社群進行合乎倫理的合作,保存獨特的聲景和音樂傳統。 Hear & Found 專注於永續性和文化認同,將藝術創新與社會影響相結合。 他們記錄並分享常被忽視的聲音敘事,促進同理心和意識。 在這六年中,他們的項目創造了易於接觸的平台,觸及全球超過25萬人,與七個以上的族群合作,並涉及這些族群中的一百多名個體,確保原住民的聲音及其豐富的文化遺產能被當代觀眾聽見並頌揚。
9. Shwe Wutt Hmon(緬甸/泰國)
《此處噪音甚響》(Noises Are Quite Loud Here)(2023-至今)
這段聲景錄製於泰國北部達府的湄波基(Maeporkee)社群,捕捉了克倫族傳統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面向:輪作農業,這是一種根植於自然再生與永續性的方法。輪作農業涉及克倫族人集體選擇一塊公共土地來種植水稻。在開始前,他們會舉行儀式向大地母親請求許可。獲得許可後,他們會清理植被、整理土地,並種植辣椒、香菜、南瓜等季節性蔬菜。年中左右,他們種植水稻,通常在十一月收成。這些作物能供應他們家庭一整年的所需。之後,土地會休耕三到七年,期間社群只會回來向土地表示敬意。這種循環方法自然地生產出不使用化學物質的有機食物,體現了再生農業的原則。克倫族人讓植物依季節生長,並收穫當季的產物,避免控制或傷害任何生物,展現了對生態平衡的深刻理解。不幸的是,由於土地權問題、年輕一代繼承意願下降、氣候變遷以及農業技術的快速發展,這項傳統知識在許多克倫族社群中正在消失。人們擔憂這種和諧且永續的生活與有機食物生產方式有朝一日可能會消失。Hear & Found 團隊對克倫族人為自己和後代保護這種農業方法的奉獻精神印象深刻,於2024年九月,在豐收前鬱鬱蔥蔥的綠色田野季節錄製了這段聲景。在這段音軌中,聽眾可以沉浸在鳥鳴、微風輕拂以及稻田隨風搖曳的沙沙聲等自然聲音中,這是他們永續生活方式的證明。這段聲景是他們《大地之歌》系列四段聲景之一,該系列交織了自然環境的聲音以及克倫族和克倫波族的音樂與歌曲。
Hear & Found 是一個由泰國藝術家Sirasar Boonma女士和Pansita Sasirawuth女士於2018年在泰國共同創立的聲音團體。出於為邊緣化聲音發聲的熱情,主要在泰國境內,該團隊創作沉浸式裝置和田野錄音,以彌合文化鴻溝並促進理解。他們的工作核心是與原住民社群進行合乎倫理的合作,保存獨特的聲景和音樂傳統。 Hear & Found 專注於永續性和文化認同,將藝術創新與社會影響相結合。 他們記錄並分享常被忽視的聲音敘事,促進同理心和意識。 在這六年中,他們的項目創造了易於接觸的平台,觸及全球超過25萬人,與七個以上的族群合作,並涉及這些族群中的一百多名個體,確保原住民的聲音及其豐富的文化遺產能被當代觀眾聽見並頌揚。《此處噪音甚響》(Noises Are Quite Loud Here)(2023-至今)
10. Lynn Nandar Htoo(緬甸/柬埔寨)
《神經網絡夜曲》(Neural Net Nocturne)(2025)
「家」的概念遠遠超出了物理邊界,它包含了記憶、文化試金石和根深蒂固情感連結的複雜性。它是空氣中飄散的熟悉香料氣味,是母語的節奏韻律,是聯繫世代的共享儀式。這些無形的元素構成了身份的基石,即使地理距離將人們分開,也將他們錨定於自己的根源。然而,無論是被迫還是自願的流離失所經驗,都可能產生一種深刻的失調感。家的舒適熟悉感變成了一隻幻肢,是昔日的回聲。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現實,一個需要適應和韌性的現實。在已知與未知之間的這個臨界空間中航行的過程,既具挑戰性又具變革性。它需要建立新的社群,鍛造新的連結,並發現意想不到的力量。最終,家的意義演變,成為一個超越物理地點的流動概念,反而存在於內心和思緒之中。
Lynn Nandar Htoo,又名LnHD,是一位來自緬甸、現居金邊的聲音設計師、音樂製作人和DJ。她被評為2024年歌德學院天才,已將她極簡且富打擊樂感的東南亞實驗性俱樂部聲音帶到國際舞台,包括柏林的Pop-Kultur音樂節。她曾在東南亞多個城市的俱樂部和音樂節表演,如仰光、西貢、峇里島、雅加達、吉隆坡、河內、曼谷和金邊。 她的作品探索身份、文化和聲音的交匯點,發行的作品如在備受讚譽的印尼廠牌Yes No Wave上的《Jamadevi》,以及在慶祝東南亞女性和酷兒聲音的平台ALIGN.ONLINE上的《SLAVE INSTINCTS》。作為Radio Lab的獲獎者,LnHD持續在東南亞電子音樂界重新定義界限,她還曾在著名的CTM音樂節上表演,進一步鞏固了她作為全球實驗音樂界新興力量的聲譽。
11. LSAC(拉哥斯聲音藝術家集體)(奈及利亞)
《感知》(Perceptions)(2025)
在世界某些地區,成千上萬的兒童在非法作業中被剝削,特別是在開採鈷、黃金和其他對全球工業(包括電子產品和電動車電池)至關重要的貴重礦物方面。然而,這些採礦活動大多在危險且不受監管的條件下進行,且多涉及童工。有些人稱之為全球供應鏈中「必要」或「不可避免」的現實,因為他們相信某些罪惡應該被維持,因為消除它們會挑戰現狀。這是否意味著某些社群應該繼續受苦和貧困,以便其他社群篡奪權力?
參與藝術家:Ibukun Sunday, Michael Akinyele, Babatunde Goodluck, Esther Essien, Olatunde Obajeun和Tosin Oyebisi。
拉哥斯聲音藝術家集體(LSAC)是一個非傳統的運動,致力於透過創新的聲音探索來重塑聽覺體驗的景觀。LSAC致力於培養一個由拉哥斯及其他地區的聲音藝術家組成的充滿活力的社群,同時推動藝術表演的邊界。透過參與式工作坊、沉浸式裝置和自發性的聲音事件,LSAC旨在讓觀眾參與一場多感官的聲音探索。我們近期的部分作品與集會包括:2023年與拉哥斯Art Twenty One畫廊合作的《聲音流變:一場實驗聲音的午後》。《創意實驗室》:一個為多樣化表演與實驗作品設計的動態工作室,2024年與《拉哥斯非洲都會》共同策劃。2025年《迴響與平衡》:一場與拉哥斯J Randle中心合作,讓聲音與個人福祉相遇的沉浸式體驗。
12. Okui Lala(馬來西亞)、Ana Estrada(墨西哥/澳洲)和Nasrikah(印尼/馬來西亞)
《重新聆聽關懷》(Re-Listening Care)(2025)
《重新聆聽關懷》回訪了《重新想像工作場所》(2024),那是由Okui Lala、Ana Estrada和Nasrikah 與照護者 Uli、Arni、Ryanie、Diane、Leeanne、Madison、Rosie、Dipin和Khushi合作創作的現場表演。該活動最初於2024年12月1日在澳洲昆士蘭美術館與現代藝術館(QAGOMA)演出,聚集了老年照護工作者分享他們的經驗並共同反思照護工作。透過重播原表演四幕中的第一幕《這是一個家》,《重新聆聽關懷》將對話延伸至第二批觀眾,強調照護工作——通常是看不見也聽不見的——值得持續的關注。透過將聆聽作為一種關懷的行動,這件作品邀請觀眾參與到照護工作中所蘊含的勞動、情感和韌性中,並將對話視為一種認可的形式和一個改變的場所。
Okui Lala、Ana Estrada和Nasrikah 三人跨國合作,透過線上會議交流想法並發展以對話、故事講述和社會正義為核心的計畫。Okui經常與家人、朋友、工人和周遭的人合作,探索身份、離散和歸屬感。Ana與老年照護中心的居民和照護者合作,探索故事講述作為連結的工具。Nasrikah是PERTIMIG的創始成員,為在馬來西亞的印尼籍家庭幫傭爭取權益。她們的合作源於對關懷、公平和集體行動的共同承諾——以及真正享受一起工作的樂趣!從《重新想像工作場所》(2024)開始,到《重新聆聽關懷》(2025)延續,她們創造了對話的空間,挑戰並反思勞動與關懷的體系。
13. Nicole L’Huillier(智利/德國)
《集體之風》(Vientos colectivos)(2025)
「大耳朵」(La Orejona)與空氣中的聲波、風的撫摸、地面的震顫以及由人類和非人類實體觸摸引發的振盪等現象互動。與常規的現代麥克風旨在捕捉單一信號不同,「大耳朵」的運作目的是將獨立的信號編織成一個集體且不可分割的噪音,一團厚重、纏繞、混濁的聲音。「大耳朵」是一個噪音的麥克風,一個橡膠質感的聆聽裝置,其核心在於「不可辨識性」的詩學。它的目的不是成為一個精確的測量設備,相反地,它是一個用來混淆信號、模糊、攪亂和遮蔽的裝置。透過這樣做,「大耳朵」旨在以一種振動的邏輯探索世界,以模糊那些劃定我們想像力的僵硬範式和界線。這是一個邀請,讓我們關注其他的編碼,以便我們能重新闡述我們的關係方式和定義我們的敘事;這樣我們才能調諧到我們的振動現實中。「大耳朵」為社會-自然安排和集體即興創作提供了一個移動式的戶外錄音工作室,透過不同的行列和集體活動,邀請觀眾的振動和互動、其所經過空間的共鳴、地方的聲音、地方的風、人聲、管樂器、合成器、樹木和植物的觸摸、水的波浪,以及她周圍的其他實體和振動力量。這件作品是以一場與「大耳朵」(XS)的集體即興行列錄音為音源創作而成,該裝置作為一個移動式薄膜錄音工作室。這場活動於2023年11月一個多雨有風的夜晚,在柏林的Morphine Raum室內外舉行,是「拉丁美洲激進聲音藝術節」的一部分。
Nicole L’Huillier 是一位來自智利聖地牙哥的跨領域藝術家和研究者。她的實踐核心是探索聲音和振動作為建構材料,以深入探討能動性、身份、集體性以及振動想像力的啟動等問題。她的作品透過裝置、聲音/振動雕塑、客製(聆聽和/或發聲)裝置、表演、實驗性作曲、薄膜詩歌和寫作等形式實現。她擁有麻省理工學院媒體藝術與科學博士學位(2022)。她的作品曾在第60屆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2024)、伯恩美術館(2024)、上海明當代美術館(McaM)(2023)、斯圖加特ifa畫廊(2023)、聖地牙哥媒體藝術雙年展(2023、2021、2019、2017)、巴登-巴登國立美術館(2022)、柏林跨媒體藝術節(2022)、林茲電子藝術節(2022、2019、2018)、智利聖地牙哥當代藝術博物館(MAC)(2022)、第6屆烏拉爾工業雙年展(2021)和第16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2018)等地展出。
14. Subash Thebe Limbu(林布旺,尼泊爾/英國)
《時空旅人的聲音紀錄》(Sound Recordings of Time Travellers)(2025)
這件作品融合了藝術家先前作品《Ningwasum》(2021)和《Ladhamba Tayem; Future Continuous》(2023)中使用過及未使用的聲音,以及一些未實現計畫的材料。這兩部早期作品都以來自遙遠未來的原住民雅克通(林布)民族的時空旅人為主角:在《Ningwasum》中,Miksam為了尋找父親而來到我們的時間線;而在《Ladhamba Tayem》中,Mikki則回到公元1774年,去見那位抵抗入侵的殖民廓爾喀軍隊的雅克通戰士Kangsore。這件作品將原住民雅克通的旋律和語言與電子音樂、田野錄音、手搖織布機的聲音,以及傳奇雅克通歌手Bhagat Subba歌曲的節錄融合在一起。在作品結尾處,出現了《Ningwasum》中的一段片段,描寫Yangdang Phongma——一個雅克通的命名儀式,新生兒會在此接受祝福,並第一次被展示太陽、月亮和星星。在這裡,時空旅人回憶起母親曾給予她的祝福:
「願你精於編織時間,
迅如光速,
亮如晨星(Tanchhoppa),
聰慧且善良。
能言千種語言,
思維百轉千迴。
永不畏懼前行,
卻也莫忘過往。
願你遊歷眾多星辰,
願星辰如我般歡迎你。
在絕望與悲傷之時,
讓它穿過你,
為更美好的明日而活。
因為我將永遠與你同在——
即使你遠在光年之外,
即使你在另一個時間,
我對你的愛,直到銀河。」
Subash Thebe Limbu 是一位來自雅克通國度(林布旺,現屬尼泊爾東部)的雅克通(林布)族藝術家,其雅克通族名為ᤋᤠᤱᤛᤠᤱ (Tangsang,意為「天空」)。他透過聲音、影像、音樂和繪畫等多種媒介進行創作。基於社會政治議題、抗爭精神及科幻/推想小說元素,他的作品以「阿迪瓦西未來主義」(Adivasi Futurism)為批判視角——這一由他多年探索形成的理論框架——深入探討時間本質、氣候變化與土著性命題。其近期作品《Ningwasum》(2021)與《Ladhamba Tayem;未來持續時》(2023)曾展出於泰特現代美術館(倫敦)、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布里斯本)、沙迦雙年展(沙迦)等重要國際平台。蘇巴什是雅克通藝術協會(Yakthung Cho)的聯合創始人,現往返於加德滿都(紐瓦-塔瑪薩靈)與英國兩地從事創作。
15. Elena Lucca(阿根廷)
《棲居、共居、復居以達復魅》(Habitar, Cohabitar, Rehabitar para el Reencantamiento)(2025)
歌聲、話語、風、夜晚、動靜、人聲、寂靜、寧靜、其他對話的聲音,一個在音樂時刻中萬物發生的空間,這讓人想起 Jean-François Augoyard的「懸浮的環境或現象學的存而不論」(l’ environnement suspended ou l’épochè, 1990),一種省略,一種對感知習慣、物體分類和先入之見的懸置,以聆聽在共居空間中發生的事,並將復居此地作為一個敏感知識的詩意過程。2025年3月,在南美洲大查科地區的雷西斯滕西亞市,氣溫連續25天維持在攝氏40至43度之間。 動植物物種以及人類,隨著時間的推移,其生命力逐漸減緩,陷入一種昏睡狀態,在寂靜中等待,直到初秋來臨時,我們才從中甦醒,伴隨著溫和的雨水、溫度的下降和濕度的增加。動靜與聲音緩慢回歸。在這個過渡中,一切都是流動的;漸逝的形式開始重新定義自己;易感的身份變得能滲透到其他快樂、慶祝且渴望對話的身份之中。在復居此地的過程中,懸念與重生在對無數細微交流和地方關係網絡複雜性的感知中浮現。每個事件都遵循其自然進程,形成一個包容性的整體。一場持續的蛻變,生命之循環,道。生命世界的詩學因此成為一場「復魅」。
Elena Lucca 是一位藝術家和環境教育家。她擁有法國亞維儂大學空間、時間與權力、文化實踐博士學位。她曾在阿根廷和義大利的大學擔任環境教育家。自1990年以來,她一直擔任法國CAIRH – Roy Hart國際藝術中心的客座講師。自1960年代以來,Lucca探索了實驗性詩歌形式,特別是透過在各國展出的錄像藝術。她還於1969年為查科的國立東北大學(UNNE)組織了國際詩歌節(Jornadas Internacionales de Poesía, JOPOE),並於1971年與Edgardo A. Vigo共同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藝術與傳播中心(CAYC)策劃了「待實現的提案國際展覽」。憑藉她在森林社群中工作的經驗,Lucca開發了一種名為「我們所棲居空間的地景詩學」的環境實驗性詩歌路線。該作品曾在多個展覽中展出,包括:《復魅》(2016)、《永恆的空間:我們所棲居之地的生態政治詩學》(2019)、《我們所棲居的空間:地球》(2021)、《我們所棲居的空間:空氣》(2021)。
16. Imaad Majeed(斯里蘭卡)
《賈拉尼的提問》(Questions of Jailani)(2025)
《賈拉尼的提問》是一件以聲音為基礎的藝術作品,探索斯里蘭卡庫拉格勒具爭議性的聖地達夫特·賈拉尼——一個神話交疊、軍事化民族主義和宗教正統派在此匯集,扭曲多元歷史的地方。賈拉尼曾是一個香火鼎盛的蘇非派聖殿,如今已成為真偽之爭的戰場——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者試圖將其重塑為一個沒有穆斯林存在的史前考古遺址,而正統遜尼派則拒絕其神秘主義實踐,視之為偶像崇拜。在這場關於起源的鬥爭中,共享的記憶被拆解,以便為單一、純化的敘事讓路。這件與藝術家Abdul Halik Azeez合作收集田野錄音而建構的作品,仔細聆聽這個空間。一名軍事人員正在掃地,而佛教的誦經聲隱約迴盪。我們聽見自然的聲音,而「阿門」的祈禱聲被拉伸成一種幽靈般的回響,擾動了人類與非人類話語之間的界線。受到一位管理員講述與附近「精靈山」(Jinni Malai)的精靈相遇的故事所啟發——那位精靈聲稱我們領域的政治是相互關聯的——這件作品將聆聽視為一種抵抗和思辨的方法。為了試圖聽見超越人類的領域及其所持有的未解記憶,它提問:僧伽羅佛教殖民的聲音是什麼?既然苦行僧(fakhirs)已不再居住於此,那在沉默中還倖存著什麼?《賈拉尼的提問》並非對失落聲音的修復,而是一個邀請,讓我們調諧於所遺留之物:迴響、縈繞,以及跨越時間、信仰和物種的糾葛。
Imaad Majeed 是一位居住在斯里蘭卡可倫坡的跨領域藝術家、策展人和作家。 他們是三語表演平台「KACHA KACHA」的總監和策展人。他們是藝術團體「The Packet」的一員,也是「Packet Radio」(SUPR FM)的VJ/DJ。他們是「Thattu Pattu」的項目協調員和共同策展人,這是一個來自斯里蘭卡邊緣地帶音樂的平台。他們的詩歌已發表於《走出斯里蘭卡:來自斯里蘭卡及其離散社群的坦米爾、僧伽羅和英文詩歌》、《CITY:南亞文學期刊》,以及當地小型出版的詩集《Lime Plain Tea》和《Annasi & Kadalagotu》。他們以各種媒介創作的藝術作品,曾在坦米爾研究研討會、酷兒坦米爾集體、Colomboscope、Chobi Mela、酷兒藝術節、奇緣藝術節、斯里蘭卡現當代藝術博物館、BuchBasel和Spielart戲劇節等場合展出。他們目前正在進行「KANNOORU」計畫,透過取樣音樂探索斯里蘭卡蘇非/穆斯林的身份、社群、記憶、抹除、祖源和神秘主義。
17. Yara Mekawei(埃及)
《以廢棄能量為食》(Feed on Wasted Energy)(2025)
一個盤子:米飯、番茄、綠花椰菜、葡萄——
培根的油滲入石榴糖蜜。
芝麻葉在沉默的重壓下枯萎。
三個女孩。一個四十度寒冬的男人。
黃色的光在他身後匯成一池,一頂黯淡的冠冕,
當他解剖他的餐點——緩慢、條理分明——
對未動的盤子、對女兒們之間
祕密縫合的眼神無動於衷。
歲月在此如地殼板塊般碾磨:
沒有意外,只有信仰脆弱的幾何。
一切環環相扣。
什麼也沒發生——
直到門裂開一道縫。
一個陌生人到來,不請自來。
廚師——他們低語——他的鬍子是
魅力的雕塑,笑聲盤繞在他喉中。
房間僵硬了。
幾分鐘如蠟油般滴落。
然後,他的要求:一杯牛奶。
他從男人手中奪過杯子,獰笑:
我曾在此抽菸。喝牛奶。沒有法律
除了我自己的。
狂野的法則展開——
一場凝視的視差。現在,所有框架都移動了:
每個身體都是運動中的星系,速度恆定,
路徑被緊身衣束縛卻又相對。沒有錨點。
沒有絕對的軸心。只有碰撞的代數:
牛奶灑了,煙霧繚繞,盤子繞著
那未說出口之事的引力運行。
Yara Mekawei 是一位聲音藝術家和學者,探索聲音、建築和城市景觀的交集。她的作品將城市的節奏轉化為沉浸式的聽覺體驗,其中聲音敘事與視覺形式融合。Mekawei的創作根植於深入的研究,從蘇非哲學和《死者之書》中汲取靈感,創作與記憶、身份和文化遺產共鳴的樂曲。她的實踐消除了過去、現在和聲音願景之間的界線。
18. Graciela Muñoz(智利)
《雲中》(In a cloud)(2025)
《雲中》誕生於2025年智利亞南極地區的奧莫拉(Omora)森林。那時,我們進行了田野錄音和傳輸的實驗:信號、回授和轉移,與那裡的昆蟲、苔蘚、地衣和發現的物體相互連結。《雲中》是那次沉浸式體驗的一個片段。
Graciela Muñoz(智利,1982)是一位作曲家、表演者和研究者,擁有智利大學媒體藝術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她在巴塞隆納的Phonos基金會獲得了電聲作曲的專業認證。她的作品匯集了在多樣的當代生態中發現的多種媒介、光譜和物質性。她目前正在位於智利亞南極地區的奧莫拉公園進行她的博士後研究計畫。
19. Jacqueline Nova(比利時/哥倫比亞)
《大地的創造》(Creación de la tierra)(1972)
《大地的創造》是一首可以歸類為「磁帶音樂」或「固定媒體電聲音樂」的作品;然而,作曲家始終強調將其描述為一首「為經電子轉換的人聲而作」的作品。它是使用檔案材料創作的,以一位來自烏瓦(U’wa)族(哥倫比亞博亞卡省)原住民的聲音,呈現了創世聖歌的一個片段。這是一個儀式,透過聆聽,文字經歷不斷的蛻變;它們從聲音中溢出,轉化為身體、記憶、領土。在這場長達19分鐘的儀式中,每一步,聲音都帶領我們與其他形式的存在相遇——可見的、不可見的、有形的、未知的、熟悉的、祖傳的。這聲音引導我們初始性地穿越世界,包括人類與非人類的,穿越塵世的、幽靈的或過渡的間隙。這首創世聖歌邀請我們化身為森林、風、昆蟲、打擊樂、合唱團、河流、夜晚。一個Nova並不屬於的社群的聲音,以及一種非她母語的語言的文字,被毫不異國情調地交織在一起,並在一個歷史上將它們邊緣化的脈絡中被放大,從而獲得了深刻的象徵價值。Nova強烈重申了平等共存的權利和無排斥存在的必要性。
文字由Ana María Romano提供。《大地的創造》,1972,由哥倫比亞國家圖書館音樂文獻中心惠允提供。
Jacqueline Nova(比利時根特,1935 – 哥倫比亞波哥大,1975)在居住於她父親的家鄉布卡拉曼加後,於1958年抵達波哥大。她定居在首都,在國立音樂學院學習成為一名鋼琴家。然而,在1963年,她轉而專注於作曲。她是第一位從該音樂學院獲得文憑的女性作曲家。1967年,她贏得獎學金,前往阿根廷托爾夸托·迪·特拉研究所的拉丁美洲高等音樂研究中心(CLAEM)學習。在Nova的藝術創作中,她對人聲、電子媒介以及混合樂器組合——即將聲學樂器與電子媒介交織在一起的組合——的極大迷戀顯而易見。對她而言,電聲資源必須被整合到當代創作的聲音宇宙中,毫無神秘感,作為另一種可以與聲學樂器有機對話的音樂材料。《大地的創造》於1972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建築學院的音響學工作室誕生。她因骨癌在波哥大去世。她悲劇性的英年早逝不僅中斷了她處於創作潛力巔峰的職業生涯,也直接影響了哥倫比亞電聲音樂的發展。
20. Lujáne Vaqar Pagganwala(巴基斯坦/英國)
《呼吸練習的剖析》(Anatomy Of A Breathing Exercise)(2024)
《呼吸練習的剖析》作為一種聲音再現,試圖將「自我」及其歸屬感的親密空間物質化。源自藝術家的「哼唱計畫」,作品中的口琴聲是她將口琴放入口中進行一系列呼吸練習的結果。藝術家使用空間分類的方法作為理解我們內在心靈和認知的隱喻。《呼吸練習的剖析》是作為「家系列」的聲音延伸而創作的。受到Pauline Oliveros「深度聆聽」的啟發,這件作品多層次地融合了藝術家在倫敦/喀拉蚩屋頂的聲音、口琴的音符和一首遙遠的搖籃曲。對Pagganwala而言,她的屋頂是心靈最深處——潛意識——的平行對照。這種描述是我們作為存在者所穿越的那些無形存在空間的隱喻。這些是不確定和潛伏的空間。在聆聽這場聲音浴時,我們同時存在於所有這些層次中。我們穿梭於每個聲音之間,不斷在這些層面之間擺盪。每個聲音都形成一個空間。每個空間都承載著我們自我的一種存在。更重要的是,這件作品意在對聽眾體驗聲音時的呼吸產生影響,因此作品也具有表演性。
Lujáne Vaqar Pagganwala 是一位對塔、結構、梯子等物體有著深厚親和力的跨領域藝術家。她探究空間的現象學,及作為一種觀念,也作為一種物理實體。Pagganwala的實踐探索在多個時空平面上同時存在的抽象存在,以及我們在這些空間中無所不在的短暫性。從童年空間和城市地貌中汲取靈感,她創造出既好玩、層次豐富又具對抗性的混合現實。她實踐的互動性將這些經驗層層疊加,形成一個永恆的好奇與生成循環。一種流動中混合能量的共存——她稱之為「閃現空間」(Flash Space)。Pagganwala獲得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當代藝術實踐碩士學位,並主要在英國和巴基斯坦之間工作。她曾在國內外主要機構展出,如泰德現代美術館、科普蘭畫廊、帆布畫廊、Koel等。Pagganwala見證了她的實踐在不同地理狀態間移動時的變形與突變。這是一種移動的實踐,永遠處於短暫之中,永遠充滿好奇。
21. Amanda Piña(智利/墨西哥/奧地利)
《以手聆聽:一種感官去殖民的實踐》(To listen with the hands. A practice for decolonizing the senses)(2025)
這是一種實踐,一趟引導之旅,一場感官去殖民的實驗。它透過聲音作用於觸摸與專注如何能轉變我們感覺、思考與存在的方式。關於感官如何能被另類使用,以及這對我們的感知有何影響。在我的工作中,我經常進行引導式實踐,旨在轉變我們思考、理解和感受我們身體的方式。今天有太多需要轉變的事物,因為我們意識到我們無法用導致其毀滅的相同工具來修復我們的家園——地球。我提議從身體開始,去轉變我們的身體經驗。這個時代邀請我們成為傳送門,允許其他的存在方式出現,其他的與世界連結的方式顯現,那些更少暴力、更少掠奪、更少恐懼的方式。這是一個轉變我們思考-感受身體方式的實踐,去反學習那些導致這場社會環境危機的過時的現代/殖民範式。這件作品只是一種實踐,與空間和他人一起進行,去探索感官,去瓦解殖民的時間性,去聆聽,去在場,去用手聆聽。我希望你玩得開心;我希望你勇於探索;我希望我們能一起成為傳送門。
致謝:這段聲音名為「暖身」(warm up),由瑞士藝術家Christian Mueller為我的作品創作,作為暖身之用。我的聲音和這段音檔由智利藝術家Marcelo Daza 混音,並在過去十年中透過與許多學生和工作坊參與者的多次教學情境中臻於完善。
Amanda Piña 是一位智利-墨西哥-奧地利裔藝術家,居住於維也納和墨西哥城之間。她的編舞作品關注宇宙政治學,包括在劇場、博物館及其他場域中存在的表演、音樂、錄像和雕塑作品。Piña是一位多面向的藝術家,透過編舞、表演和舞蹈研究進行創作,在大學和藝術教育框架內進行創作、策展和教學,並圍繞她所稱的「瀕危人類動作實踐」撰寫和編輯出版物。她的工作根植於原住民的知識形式和創造/維護世界的方式。她的作品曾在世界各地的劇院、畫廊、博物館和文化中心展出,例如維也納舞蹈區、維也納藝術館、維也納現代藝術博物館、安特衛普deSingel藝術校園、巴黎卡地亞當代藝術基金會、墨西哥大學Chopo博物館、墨西哥、GAM和智利聖地牙哥等。2024年,她獲頒柏林自由大學的Valesca Gert編舞系主任。
22. Ruhail Qaisar(拉達克)
《ZANGRNAMS》(2025)
「我面前是原始的天空,虛空,空無
一陣黑風升起並盤旋,火焰熾燃
峽谷的兇猛紅靈出現在我面前
祂額頭中央是原始覺知的眼睛
身披猩紅斗篷,祂站在一匹紅色的神馬上
祂刺穿我的心臟
血液如海洋的洋流般湧出」
這首樂曲的構想源於七個惡魔兄弟或稱「贊」神的傳說,他們來自康區(西藏東部),並在拉達克定居,成為寺院和神諭的保護者。這首樂曲以他們中最年輕的Zangrnam命名,祂是一位兇猛的神,每年要求三次血祭——傳說延伸至說這位神祇曾下令要一顆八歲孩童的心臟,後來這個祭品被一隻白山羊取代。現今,在Skurbuchan村莊盡頭的一個杜松樹林下,會用一塊肉作為替代品。這首樂曲是對這一儀式行,其恐怖以及這種特定殘酷性的戲劇性的聲音詮釋。
Ruhail Qaisar 是一位來自拉達克列城的藝術家。他目前的實踐圍繞著透過聲音藝術、作曲和拾得雕塑來檢視地方記憶、神話和詩學的線索。自2015年以來,他參與了各種跨類型項目,他在全印度的早期噪音演出被譽為「聲音的味覺清新劑」。他以概念專輯《Fatima》(2023)出道,被《The Quietus》雜誌稱為「縈繞心頭」,由Danse Noire廠牌發行,並附有一本48頁的攝影集,專輯中還邀請了Dis Fig和Elvin Brandhi合作。他為Les Urbaines藝術節委託創作、與Gottfrid Ahman和Michael Anklin合作撰寫的聖歌作品《Three Hymns of Cruelty》(2022),深入探討了拉達克儀隊音樂的動態,並在洛桑的Arsenic演出。他的拾得錄像帶短片《Cenacle 97-98》(2022)曾在蘇黎世美術館、La Becque和蘇黎世Gessnerallee的Parasite O Sinensis活動中放映。他最新的作品《Gods Erupt Like Tumors》是一系列拾得雕塑和一個單聲道聲音裝置,正在瑞士比爾斯費爾登的Salts畫廊展出。他最近完成了在奧地利格拉茨的駐村,為ORF(奧地利廣播集團)的Musikprotokoll音樂節和Steirischer Herbst ’24藝術節準備了一個36聲道三階高保真環繞聲作品《Namkhay Rtsima/天空之脊》,將在Dom im Berg 演出。
23. Superlative Futures(新加坡)
《聽潮(無常之聲):尋找普陀》(2025)
2025年2月15日,新加坡。
晚上7點30分,低潮位+0.30米。
我們離開城市,希望找到普陀——但不是那個地名所指的山(也是一座島嶼)的地理位置。相反,我們找到的是一個隱喻性的普陀,在一個每月一兩次低潮時才會顯現的潮間帶變幻邊緣。潮水退去而後又返回岸邊的節奏性聲音,讓人想起普陀山腳下那個可以聽見潮汐變化的洞穴。據說,正是在那裡,觀音菩薩(其名意為「觀察聲音者」)透過聆聽潮水的來去而悟道。
《尋找普陀》(2025)是一件15分鐘的聲音作品,以循環的方式重述藝術家從市中心到海岸邊緣再返回的身體移位過程。當潮聲變得可聞時,水泥城市的堅實感在腳下消融,化為泥濘的物質無常性。這件藝術品呼籲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停下來,觀察潮汐的聲音。每一次的來去,都是一個找到我們小小普陀的機會。
Superlative Futures 是新加坡的一個跨學科設計與研究機構,由Wong Zi Hao和Liu Dian Cong共同創立。該研究實踐以創意的再現模式為核心,倡導新的觀看地景方式,並為城市推測另類的社會想像和未來實踐,以更好地與超越人類的世界建立關係。他們將其設計產出視為一種關懷的實踐。他們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博物館展出,並獲得新加坡美術館首屆設計研究獎學金(2024-2025)的支持。Wong於2023年獲得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學博士學位,完成了一項關於潮間帶關懷實踐的設計導向研究。除了研究實踐,Wong還在國立大學建築系和新加坡藝術大學(南洋藝術學院)的設計實踐課程中任教。Liu在2024年完成國立大學建築碩士學位後,目前從事建築設計師工作,探索沉積作用和對「地」的另類概念。
24. Irazema H. Vera(祕魯)
《Puna(源自克丘亞語、毛利語)》(2025)
是泉源,也是安地斯高地區域。(Es manantial y también la región de las alturas andinas.)
是開端,是流動的泉水,是靠近天空的輕盈。(El inicio, la fuente que fluye, la ligereza de estar cerca del cielo.)
在這件作品中,我探索記憶與連結的聲音:與我們起源的連結、與我們所生活世界的連結、與我們創傷相關的連結,以及那些呼喚我們靈魂回歸以繼續前行的聲音。正如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日子之子》中,為我的生日8月11日所提到的,在他對原住民智慧中家庭/whānau/ayllu意義的詮釋中:
「……
你的家人也在火的爆裂聲中對你說話,
在流水的潺潺聲中,
在森林的呼吸中,
在風的聲音中,
在雷的怒吼中,
在親吻你的雨中,
在迎接你腳步的鳥鳴中。」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日子之子》)
在紐西蘭的奧特亞羅瓦,whenua一詞既指土地也指胎盤。因此,我的女兒 Puna,從宇宙-子宮-hapu中出來,離開了whenua,被另一個whenua擁抱,找到了源頭,找到了la puna。
錄音於2019年11月至2025年2月間在紐西蘭奧特亞羅瓦的Te Awanga、Waikaremoana湖和奧克蘭(Tamaki Makaurau);以及祕魯的普諾、Caritamaya(艾馬拉國度)、Chua Chua(奇洛國度)和利馬進行。
Irazema H. Vera(普諾,1983)是一位祕魯藝術家、音樂家和音樂學家。她的作品圍繞著記憶、音樂和領土;範圍涵蓋聲音工程、音樂製作、紀錄片與敘事性播客、聲音藝術和研究。她以田野錄音和聲景作為其藝術實踐不同路徑的起點,在其中,記憶透過人聲的見證、音樂以及脆弱和受侵犯領土的聲音來表達。她的作品包括她文化遺產來源地普諾高地的克丘亞和艾馬拉文化的音樂傳統和地景,並曾在拉丁美洲SONODOC、巴勒斯坦Radio AlHara、荷蘭RRFM、祕魯Común Radio、英國Cities and Memory,以及廠牌 MATRACA(祕魯-墨西哥)和Eck Echo(祕魯-柏林)的合輯中發表。
25. Valentina Villarroel(智利)
《它們是我的聲音》(They are my voices)(2025))
它們是我的聲音,
一片無盡織物的碎片。
我與葉的低語融合,
與火車的遠方歌聲,
與雨的液態節奏。
我模仿,我重複,我重塑自我。
Valentina Villarroel 是一位聲音藝術家和聲音記錄者,她探索各種南方生態系統中錯綜複雜的動態。她的作品圍繞聲學生態學的深遠潛力,特別是在面對不斷侵占自然空間的房地產開發時。她也深入研究聲音污染對眾多物種的後果,這些污染導致牠們的數量下降或消失。近年來,她的關注點擴展到城市聲景和重要的聲音事件,例如智利的「十月十八日」抗議活動。她在應用於人類和動物福祉的生物聲學方面擁有堅實的背景。她的專輯深入探討了可聽與不可聽聲景的世界,以及它們賦予我們對現實另類認知的能力。
26. 嚴瑞芳(香港)
《黑鬼蹤跡》(Black Ghost Trail)(2025)
聲音或聲音遊戲如何能喚起記憶或重新具現化一個地方的感受?受到香港本地客家村落川龍一位居民在60、70年代童年經歷的啟發,這件作品探索了他年輕時在自然與人造元素中的生活,例如來自大帽山的溪流、一條充滿風和松樹的山路,以及墓地周遭的環境。對於城市居民來說,與各種物種互動、玩耍和感知的能力似乎已經喪失。我們能否重新奪回這種開放性,作為對同質化城市生活的一種抵抗?以聲音為載體,將過去與現在編織在一起,並作為參與村落記憶的一種方式,我使用田野錄音來記錄和重組川龍村。這包括尋找線索、創造遊戲、玩耍和漫遊,以引發新的反應。剪輯過程就像一場反覆出現的聲音遊戲,喚起幽靈般的童年記憶。
嚴瑞芳 是一位駐香港的藝術家,同時也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助理教授,她的實踐跨越社會參與藝術、集體學習和聲音。透過參與式聆聽環境和以聲音為基礎的裝置,她活化了記憶和共享的能動性——取材於口述歷史、次要檔案和特定場域的聲景。她的作品將聲音框定為一種抵抗的媒介和一種協作知識生產的方法。她是「天台塾」(Rooftop Institute)的共同創辦人,倡導將藝術學習作為一種社會參與的模式。她也擔任HASS Lab的董事會成員,推廣由藝術家主導的社會包容方法,並且是「參與的生態」的發起人之一,這是一個連結實踐性創作與公民參與的跨學科平台。作為香港藝術發展獎青年藝術家獎(視覺藝術)和WMA大師獎的得主,Yim的實踐典範了社會參與式聲音藝術如何能催化交流、放大被忽略的聲音,並預演集體記憶的新形式。
27. zeropowercut(印度)
《bujhat naikhe》(無法理解)(2024)
這首歌是對陽剛特質的反思,講述一個人在自己建造的茅草屋裡尋找自我的故事。這首歌以博杰普爾語演唱,探索了「尼爾古恩」(Nirgun):一種思維和歌唱的形式(一種藝術形式和一種哲學)。簡而言之,「尼爾古恩」是認識到世界和事物是無法掌握的,因此,透過物質性和經驗來實踐智性(和可理解性)。這首原創歌曲是一部名為《Lattar》「藤蔓」的音樂劇製作的一部分,該劇探討了「那奇」或「Launda Naach」藝術家的生活,他們因「男扮女裝」的實踐而在這個父權和種姓封建的世界中聲名狼藉。這首歌由已退休的Launda Naach藝術家Sunaina演唱(人聲和音樂),由戲劇專業人士兼歌手表演者Raju Ranjan與獨立研究者兼藝術家Piyush Kashyap合作撰寫。《Lattar》是由位於印度班加羅爾的媒體與藝術團體Maraa為其2024年十月名為「石頭花」的Jam活動所委託創作。zeropowercut也感謝Sipahi,一位那奇藝術家及Lattar團隊的共同成員,以及Puneet,他在《Lattar》製作期間慷慨地提供了食宿。
zeropowercut創作藝術是為了找出壓迫如何隱藏在平凡之中。他們談論自我貶抑和解離,專注於基於種姓壓迫的各個方面「首陀羅化},這種壓迫從即時到歷史和文明領域,抹殺了勞動人民體驗和獲取知識的能力。
zeropowercut 在霸權性邊緣化和被剝奪的「我們-的-起源-世界」中生活和工作,以個人和集體的方式創作作品,常常將生產場所轉變為原本隔離的社會性和文化的交匯點。zeropowercut使用日常物品、俗語、語言、聲音和氛圍來創作裝置、互動、歌曲、戲劇和研究報告,主要使用演講、紀錄片和散文的模式。